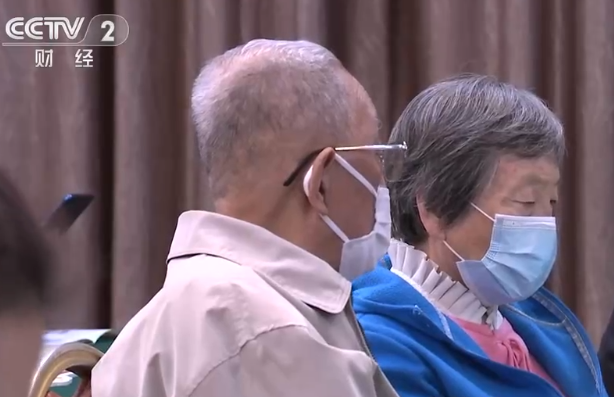《原野上的声音-彝族合辑》专辑封面
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2019年1月,两位四川“95后”音乐人吉尔赤沙、刘俊麟发起“原野上的声音”彝族民间音乐采集计划。团队深入四川凉山和云南相关地区,采集彝族等少数民族民间音乐,经二度创作制作完成专辑《原野上的声音-彝族合辑》。
不久前,这张专辑正式上线各大音乐平台,11首不同内容、风格的作品,以及包括莫西子诗、泰然等知名音乐人在内的强大创作阵容,引来不少音乐爱好者关注和好评。3月4日,吉尔赤沙、刘俊麟与团队举办了“重回兹兹普乌”成都专场演出,大家穿上彝族服饰、跳起达体舞,对几年来采集计划的成果进行集中展演。
“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,民族传统文化在每一个时代都应该创新转化,但创新不代表丢弃传统。”吉尔赤沙和刘俊麟表示,今年,“原野上的声音”还将继续出发,开启藏族民间音乐采集工作;同时,思考和探索从民间到舞台的方式,与文化产业结合,为民间文化创造市场,发动更多人自主学习、创新、传承民族民间音乐。
吉尔赤沙(前排左二)、刘俊麟(前排左四)和“原野上的声音”团队成员与采风对象合影
一场“文化寻根”,催生民间音乐采集计划
刘俊麟是达州人,曾作为国内某少年偶像组合的一员,在央视、湖南卫视参加节目。不过,他对民族民间音乐的兴趣,其实可以追溯到家乡。
“我小时候学习架子鼓和扬琴,10岁就写了第一首作品。达州城区有一座凤凰山,经常有人在上面唱民歌,听着听着就有了兴趣。后来在电视上看青歌赛,我也只看原生态那个组。”组合解散后,刘俊麟于2016年到成都做音乐。
那段时间,出于对世界各地民族音乐的喜爱,他就经常前往四川少数民族地区采风。“线上音乐时代,听到什么都觉得似曾相识。”刘俊麟希望通过采风,为自己的音乐创作积累更多素材、灵感。
在一个音乐节上,刘俊麟偶然结识了吉尔赤沙和他的乐队。吉尔赤沙出生于凉山州甘洛县,在外公外婆身边长大,用他自己的话来说,“从小就放牛、下河游泳,有一段很快乐、很难忘的童年生活”,直至初中离开家乡外出读书。
从那时起,吉尔赤沙每年只有寒暑假才有时间回老家,看看自己儿时生活、成长的地方,随着时光不断流逝,他敏感地发现家乡也在不断变化。“以前‘火塘’是生活的中心,好像什么事情都发生在火塘边上,但慢慢地很多人住进了新房,火塘变成了‘小太阳’、电磁炉。”再加上彝族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,留在家乡的普遍是老人和小孩,对于从小就喜欢唱歌的吉尔赤沙来说,音乐场景“肉眼可见地”变少了。
“那时候,我就希望做点什么。”一开始,吉尔赤沙没想太多,只是计划在每次回乡的时候,通过文字、图片记录一下飞速变化的人和事,争取过几年出一本书。后来他忽然意识到:既然想要传承、传播彝族文化,为什么不用音乐的方式,让更多人听到、感受到呢?“我自己有创作能力,但没有制作和编曲能力。”跟刘俊麟碰撞想法后,两人一拍即合,很快开始商量采风的形式、地点、内容、费用等细节。
2019年1月,吉尔赤沙和刘俊麟正式组建“原野上的声音”团队,致力于民族民间音乐采集与二度创作。“从我们开始商量这个事情,到第一次出门采风,只用了一个星期。”他们带着几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,揣着仅有的1.4万元,开着一台租来的商务车前往凉山腹地的美姑、昭觉,当年夏天又继续探访布拖、甘洛。
2021年夏天,这支全员“95后”的团队,又将脚步踏出四川,前往云南楚雄、大理、丽江等地,既寻访彝族聚居区,也寻访纳西族、傈僳族等少数民族。“试图找到民族文化、民族音乐与现代音乐的结合点,在保留音乐原始性的前提下,让更多的人听到这片原野上的声音。”吉尔赤沙和刘俊麟说。
漫无目的地游荡,却时常带来“意外惊喜”
这次采风,“原野上的声音”团队没有提前规划日程和路线,也没有联系目的地文化部门、民间艺人,而是在当地随机应变、“走到哪里算哪里”。
这种方式看似“不靠谱”,其实意在避开过度“舞台化”的民间音乐。吉尔赤沙认为,团队需要的不仅是音乐素材,更需要一种源自灵魂的生命体验。刘俊麟也表示,由于后期还涉及二度创作,因此采风过程中的感受也非常重要。
采风中的吉尔赤沙(左)和刘俊麟(右)
于是,在他们的采风过程中,这样的场景可谓常态:后备箱装满了烟酒、糖果、酸奶和其他小礼品,漫无目的地在乡间游荡。有时候在路边遇到一群彝族村民,大家便停下车、送上礼品开始聊天,打听村里有没有会唱歌的人,有没有会演奏乐器的人。“这样既能增加采风的体验感,还经常带来意外惊喜。”吉尔赤沙说。
采风中的吉尔赤沙
采风中的刘俊麟(左)
刘俊麟(左)和吉尔赤沙
在美姑县,他们在路上偶然发现一个不错的点位。听闻有人前来采风,村民们迅速把消息传遍了整个村子,当他们进村的时候,就看见“乌泱泱一群人从山上跑下来”,手里拿着口弦等民族乐器,都很开心。“原野上的声音”团队迅速分工,刘俊麟带着一群彝族妇女在室内录制,吉尔赤沙跟一群老大爷聊天,获取更多的文化信息。几个小时的时间里,大家就录制了十几段音乐,包括歌曲和口弦乐曲。
2019年夏天,团队在布拖采风时,恰好遇上彝族火把节。“我们在县城广场上找人,认识了一位毕摩。”大家跟他聊天,送他回家,半夜12点在家里录了几段。“路窄又有蛇,不小心开错了,结果整整倒车两公里。”刘俊麟说,他们后来创作的歌曲《兹兹妮扎》,就在开头加入了此次录制的一段采样。
在云南采风时,有一天,大家原本计划前往巍山县,采集一些民歌和吹管类器乐,没想到半路遇见两位彝族阿嬷,得知她们村里有“打跳”活动,于是改变当天的行程。在那里,一位大叔特意给他们吹奏芦笙,一位阿嬷演唱当地民歌,他们还领略了极具当地特色的“打竹刀舞”。
“我们遇到的这些民间艺人,他们都不懂现代的乐理体系,什么和声啊、节奏啊,但是他们所演奏、演唱的东西,我们用记谱的方式可能也无法记录清楚。”刘俊麟说,更重要的是“见到了日常生活中见不到的不同精神面貌的人,甚至对人生观、价值观也会重新产生思考”。
探索“二度创作”,让更多人走进民族音乐
从2019年初到2021年夏天,“原野上的声音”团队在将近3年里,采集彝族民间歌曲、民间故事、器乐曲共计500余段。他们没有仅仅满足和停留于此,而是接下来展开二度创作。
刘俊麟介绍,民族民间音乐的二度创作通常有三种方式:一是在既有音乐旋律基础上,利用一定的作曲法进行改动、改良;二是用电子音乐的创作方式,对既有音乐“切片”“重组”成另一个旋律;三是抓取原有音乐素材的旋律特性,以此为基础进行原创。在《原野上的声音-彝族合辑》中,他们对三种方法都有尝试。
前者最典型的案例,便是专辑中的《哭嫁歌》,这也是整张专辑中唯一的纯彝语歌曲。刘俊麟说,《哭嫁歌》的原曲,原本是美姑县井叶特西乡一位彝族妇女演唱的民歌,采风结束整理素材的时候,这首曲子让众人眼前一亮,大家发现它的旋律走向比较忧伤,于是对其进行改编、填词、编曲成为如今的面貌。“在音乐平台发表之后反响很好,很多人留言讲述‘喜欢的人没能在一起’那一类故事。”吉尔赤沙说。
在他们的二度创作中,听众能领略到不少彝族传统文艺形式,例如《五公》一曲,主体内容便来自彝族克智。彝族克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有固定格式的诗体文学,内容有抒情、有叙事,丰富多彩,主要在娶妻嫁女的场合表演,男女亲家两方各自选出能说会道、思维敏捷、知识丰富者为代表,边饮美酒边展开舌战。《五公》在彝族克智的基础上结合了凯尔特音乐元素,加入月琴与口弦,增强了曲子的民族感与韵律感。
“相比做乐队或者原创音乐,二度创作的难度更大,因为它不能凭空创造,需要更多积淀和想象力,对自己也是一种锻炼。”刘俊麟说,从世界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来看,无论早期的爵士乐、布鲁斯音乐,还是时下备受瞩目的嘻哈音乐等,其实都有着民族民间音乐的根与魂。吉尔赤沙则希望通过这样的作品,引导更多听众走进和聆听民族音乐,吸引更多人从事民族音乐的采风、保存、研究和创新。“将来条件成熟之后,建立一个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曲库,对采集的作品分类整理上传,吸引更多人采集、上传作品,既可以供学者研究,也能让本民族的音乐爱好者追根溯源。”
“说得更大一点,也想让大众对本土音乐文化更自信一些,不要听到合成器就觉得是‘洋’的,听到唢呐就觉得是‘土’的。”刘俊麟说。
“‘原野上的声音’启动的时候,我23岁,现在28岁了,感觉自己在随着它成长。”吉尔赤沙说,尽管这是没有回报的事情,但浸润在民族文化中,自己无时无刻都觉得很幸福,觉得“真真切切地活着”。“希望未来的采风覆盖更多少数民族,二度创作的作品能走到国外,对民族音乐的传承创新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。”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